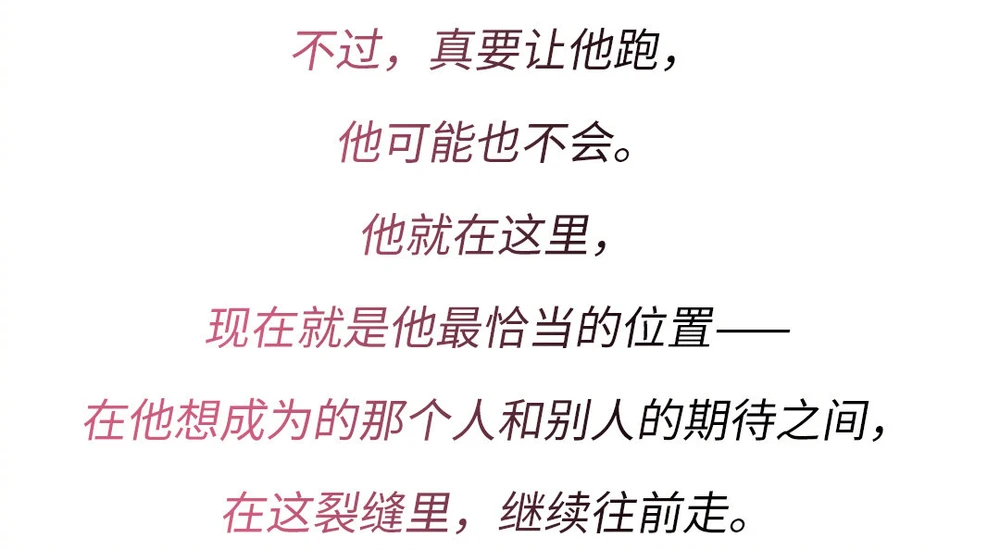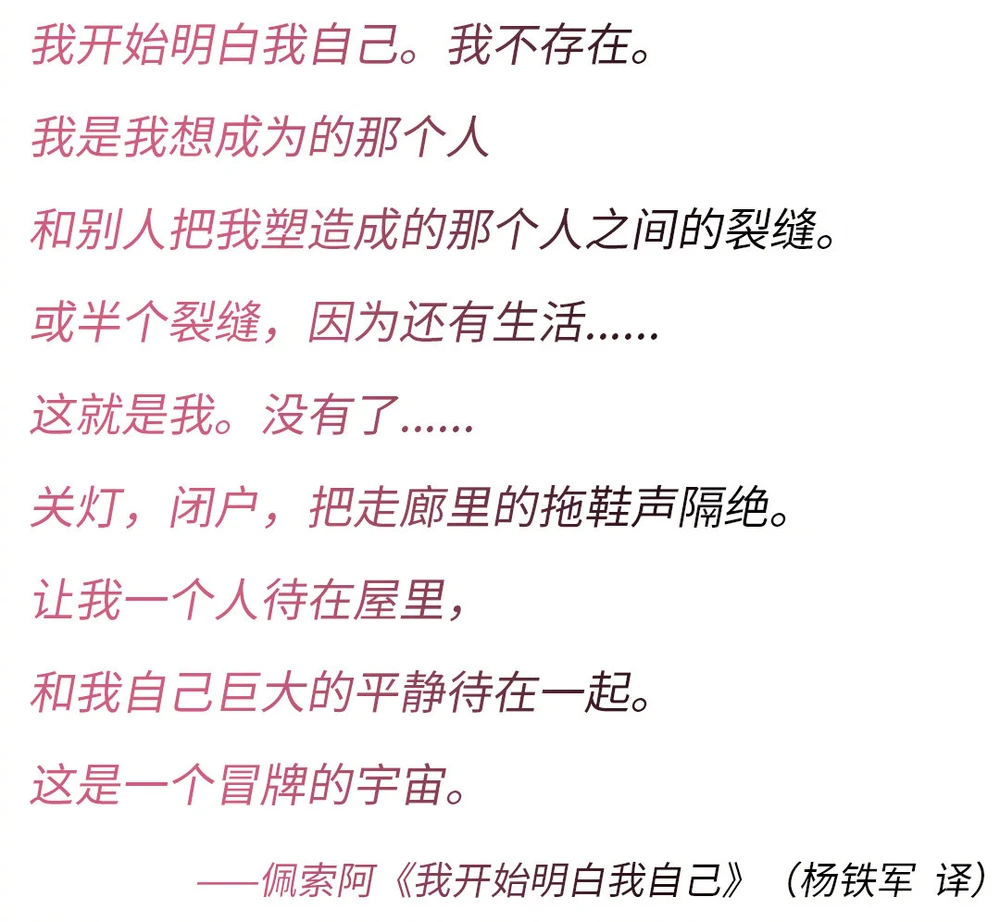


“早就有两个肖战了,其中一个在这儿,就是我。”二月初,重庆仙女山景区,拍戏中途,肖战一边吃饭一边说。“还有另一个肖战,加引号的肖战,但他可能已经不是我了。我们都为他工作,包括我自己。”
肖战放下筷子,张开两手,手心相对,像是在比划一个无形的小箱子。
跟以前一样——跟大部分人一样——真没有什么特别——只想把这个工作干好——根本没想那么多——不知道还能做什么——就是一个人待着——在关于肖战的叙述当中,无论肖战本人,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,时不时地,面对悬浮在空中的一个一个问题,他们只能以这些句子作结。
对于一位明星,大部分人的心态可能是矛盾的。一方面,人们习惯了贴着标签的世界,依靠几个词语就想概括一个陌生人,不愿费力;另一方面,探究真实的冲动又时时吸引我们去质疑标签,寻找更熟悉的情感和人性。在肖战这里,这个矛盾尤其突出:他的标签少之又少,没人能找出最准确的那几个;与此同时,越是接近他的人,越是发现,他的人生正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种——正因为太过熟悉,反而又怀疑它不是真的。这矛盾像个裂缝。肖战就在这个裂缝里做着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。
1. 山上的小屋

小时候,通常是过年前,为了祭祖,肖战要去爬一座山。那时他觉得,重庆真太大了,山那么远,为了爬山要走那么漫长的路。早晨,才睡醒,跟着大人,先从家里出发,坐公交车到枢纽站,转车,从重庆的南区到了江北,跨过江水,才来到山的入口处。那是90年代,那条山路当时还是泥路,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村里人靠脚走出来的。路边是野草,路窄,不到一米宽,车子开不上去。肖战记得,记忆中脚下的山路时隐时现,一会儿清晰,一会儿模糊,赶上雨天,路上很滑,小孩子们跑在前面。小孩总是冲在最前面,大人总是跟在后头喊,错了,错了,不是那边,是这边。
没有坐标,没有导航,肖战和家人只能凭借着记忆去寻找那座山路边的祖宅。那是一座棕黑色的木房子。房子可能有一百年了,曾经住着肖战奶奶的父辈,或者奶奶的祖辈。当然,现在早已经没有人住。肖战在老房子里走,他记得一层是两个卧室,二楼也是一个小卧室,一楼通向二楼,有一座木梯。一座老的灶台,烧的是柴火。整座房子都是木质结构,房屋外面是一个小院子,里面好像还有一棵石榴树。

这是大家庭里一趟必不可少的行程。到了山上,活动不少,肖战和哥哥姐姐采野葱,拔萝卜,挖野菜,也一起试着生火做饭。玩累了,有时他也试着自己待一会儿。他看见大山后面还有小山,于是离开家人,往那些小山丘上爬,开始一场小孩的探险。到了山丘背后,四下无人,他一个人静静待在那里,看着青黑色的远山。家人们往往会在山上待一天,直到傍晚才下山。
“小孩子是不会害怕的,”现在他回想当时的自己,“只有长大了的人才会。”看着朦胧的远山,他真想走过去——小孩最不缺的就是勇气——那时他觉得,再难的路,手脚并用也能爬上去。但后来,慢慢年龄大了,升到中学,到了大学,再来这座山,他反而不敢像小时候那样大胆随意地攀爬了。
最近一次去这座山,是几年前了。如今已经新修了路,高速公路能直接通到山下。肖战和家人开车来到山脚,但山还是要双腿去爬。他们走向那条多年来一遍一遍走过的路。小时候,肖战觉得,大人的腿长,走起来那么快,但现在,他在重庆待得越来越少,发现父母上了年纪,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。他和哥哥姐姐拎着行李,一步一步,记忆里那漫长到令人疲劳的旅程——要经过那么多地方,比如一片竹林,一片坟包,标志着一段又一段里程——这次却好像缩短了,不知不觉,没走两步,就到了那座老宅门口。一路上回头看,小时候的大片竹林现在看着只是一小堆。原来觉得恐怖成群的坟包,现在好像只有三两座。还有那些小山丘,小时候,爬上去要花那么久,现在,似乎只需要轻轻抬脚,一步就能登上去。至于那些记忆里陡峭的山脊,现在好像坡度也都下降了。泥路没了,黑色的柏油盘山公路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山上还建了度假村,农家乐,还有不少的观景台。
山曾经那么远,那么高,肖战现在想,但随着时间过去,山不再远,也没有那么高了。当时,他只是个普通的重庆小孩,现在,很多人都知道肖战。不过,没变的是,这座山还是没有名字。
2. 梦中的厂区
现在,肖战还是会梦见小时候住过的地方,那片当时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厂区。厂区好像属于某个汽车零部件生产公司——一小区、二小区、三小区、四小区、五小区——他都忘了自己具体住在哪个小区了——厂区的房子都很像,七八层楼高,一幢幢,在记忆中是灰扑扑一片。厂区里有很多同龄的玩伴。写完作业——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——孩子们就会跑下楼,叫声此起彼伏,回荡在半空里。“某某某快点下来!某某已经下来啦!”玩到八九点钟,妈妈们又会在窗户上伸出头,在夜色里遥遥往下喊:“某某某,回家了!某某,睡觉了!”

踢球,捉迷藏,躲在草堆或是转角,一些黑暗的犄角旮旯。厂区里最可怕的地方是一条废弃的下水道,洞口很大,人那么高,里面黑黢黢的,什么也看不见。偶尔有蝙蝠飞出来。胆大的孩子,点燃一根火柴就往里面走。肖战从没进去过,洞里太黑了,他远远看着他们。
摔伤是家常便饭,孩子跑着跑着就会摔在地上,肖战也是,他的膝盖上留下了不少的疤。现在,看着那些孩童时的伤疤,他反而觉得那可能才是更真实的生活。现在更像是虚假的,虚幻的。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,当时的生活,好像每个瞬间都还在这,像拍下了照片,停在记忆里,留在心里。肖战现在还记得,父母有时候不让他下楼,担心他玩得太野。他一个人待在房间,趴在窗户上往下望。他现在还能想起当时眼前的所见——邻居家的阳台,阳台上的花盆,晾的衣服,楼下的花园,花园里的小径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小学读到三四年级,他叠飞机,把纸飞机从五楼往下扔。一只飞机飞得很远,一直飞到了隔壁楼的阳台。他还经常梦到在厂区里奔跑,在那些作为小孩奔跑过的地方。在这些梦里,肖战不像是离开过这里,再回来。他记得梦里的心情——自己还是住在这里,现在只是玩累了,爬楼,回家,想去卧室睡一觉。
那时肖战的家在五层。上楼梯时,楼道老化,很多灯已经不亮了。每次走到第三层,出于对黑暗的恐惧,他都要深吸一口气,“砰砰砰”地冲上四层,到四层就有灯光了。现在,每隔一段时间,他还会时不时地梦到那个黑暗的三楼过道。梦里漆黑一片,什么也看不见,不知道角落里有什么东西。还有一次,他印象很深,在梦里他已经穿过了三楼的黑暗,来到了五楼,但依然没有灯光。面对熟悉的房门,梦中的自己伸出手,费力地想拧开门,拧不开,握起拳头敲门,屋里没有人。他怎么也打不开那扇门,就在梦中的楼道里徒劳地站着。

跟其他人一样,有时肖战也会梦到考试。每次他都会惊醒过来。有次是一位数学老师,有些凶。其实他挺喜欢那个老师,但在梦里,老师看着他,说,你怎么回事,怎么一道题都不会做?他看着书上的函数,傻了,“我怎么还记得函数呢?一道题都不会做,完蛋了。”
厂区就是整个世界,它几乎广阔无边。要出厂区,得提前和父母报告,就像是出趟国。那会儿他读百科全书,一套有四本,其中一本讲述地球与宇宙,书上有张图,画的是地球剖面图,地表下还有许多层。他想原来地球是这样,于是想起楼下花园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。他后来喊小伙伴一起来到那块石头前,提议说,我们搬开它,下面就是岩浆,就是地球真实的样子。
现在回想,当时这样的想法幼稚可笑,但他细细品味,还是不知道自己那时候为什么如此执着于那块石头,执着于地球的真实面貌——只是一块普通石头,一个小孩,却想从它背后看到整个宇宙。
3. 山城

肖战记忆中的重庆很老,又很新。电影院里,他记得,90年代,父母带着他看《黄河绝恋》,《宝莲灯》和《狂蟒之灾》。去解放碑时,要挤公交车。真的很难挤上去。大概每个人都想占座吧。他不记得具体是几路车了——可能是3开头——上车后,人们会因为座位吵架,有时还会打架。那路车太热闹了,永远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。站在车上,肖战看着窗外,公交经过下城区很长一段寂静、安详的道路,车窗两边显现出有些古旧的老城模样。但是,过了长江大桥,一下子,他就进入了一个开朗、现代的摩登都市。已经是上城区了,那时候,重庆已经开始建起高楼。至于下城区,原来靠江的地方最多的就是那些老房子,现在早就拆掉了大部分。那样的城景很迷人,肖战现在想,好像自己身处在历史中,在那些逗留不去的沉稳的过去中,一抬头却又能看到高楼大厦上耀眼的玻璃幕墙,好像那些神秘的去往未来的东西就要把自己带走。
还有渝中区的大田湾体育场。甲A时代。重庆的主场那时可是火遍全国。父亲带他去看球,重庆力帆,1997年,1998年,1999年,2000年——重庆队最好的那几年——体育场常常真就坐满了几万人,大家齐声高喊“重庆,雄起!”肖战那时小,看不懂,望着满场的密密麻麻的人头,只是觉得热闹。
那还是读报纸的时代。小时候,肖战家里一直订《重庆商报》,他喜欢看报纸,那么多页数,他几乎都会翻完。后来,又过了几年,长大了,地铁轻轨上还有免费的《重庆晨报》,他也习惯性地取来一份。一般是先看社会新闻,从头到尾看一遍,有时候,报纸看完了,地铁还没到站,他就翻到头版,从头往后再看一遍。
那也是交笔友的时代。学校里,老师鼓励学生交笔友——也许是为了锻炼写作文的能力——他也交上了一个,相互通信,聊天气,阳光,重庆的雨。不过,通信就两回。不过,他还记得那种等待自己信件的状态。写出信,才隔了一周,他就来到学校的传达室,查看班级的信箱。手往上一掰,打开铁盒,从那厚厚的一叠信封中,寻找写着“肖战”两个字的来信。
时间按照某种流水般的秩序往前。初中。高中。大学。考大学,填报艺术类志愿,他的分数超过了重庆分数线,也可以去参加全国其他学校的校考。老师问肖战,你确定要选重庆吗?要不要出去试一下,比如去北京或是浙江,去国美看看。
他说不要。肖战很明确,重庆挺好。他太喜欢重庆了。如果不是做演员,不用去那么多地方,他也许就一直待在这里。不过,他现在也想,一切也都是未知,如果有一个平行世界,他可能也早就不在重庆了。不是刻意要走,也不是刻意要留,只是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地,不是非得去哪里。

现在他已经忘了那条上班的路叫什么名字了。朋友介绍,他投了简历,面试通过。那家设计公司在重庆一个产业园区,他也记不起来是二楼还是三楼了。走进去,一排一排工位,公司不大,十个人左右。早上九点上班,晚上六点下班,打卡两次。他从家里出门,坐公交,过一个桥。有座位的时候就坐,没有就站着。有时候堵,有时候不堵。上班开会,他溜边坐——跟大部分人一样吧——他要坐在离老板最远的位置。工作主要是做图和画图。他们戴着耳机,听着歌画图。办公室整个氛围比较昏暗,暗暗的工业风,空调在室内发出闷响。赶上阴雨天,屋里就更暗了。他不抽烟,靠近坐在工位上抽烟的同事,偶尔空气有点烟雾,他也觉得无所谓。有时候,如果客户要的东西急,他们还得熬通宵加班。早上出来,头有点沉,肖战走到附近便利店,随便买些什么小吃。
下班的时候如果正赶着下了雨,那就有点烦心。肖战要走一个上坡去坐公交,雨水沿着马路往下流,他迎着走上去,相当于逆流而上,没几步,鞋子就全湿了。本来就累,全身又被水淋得黏糊糊的,现在鞋里又钻进了水,他烦躁地站在那里等公交。下班人多,第一班车可能上不去,那就继续站着,再等下一班。
工资发了,他交一部分给父母,自己留一点。他不抽烟,不喝酒,最多跟朋友去KTV,很少逛商场。得换季的时候真缺衣服,他才想着去买两件。这种习惯一直保持着——缺什么,买什么,而且是直接去买,绝对不会先去逛商场。
4. 脸与戏
现在,起床以后,肖战站在镜子前。镜子里的他头发凌乱,有时候脸有些肿。他想,如果被人看到这副模样,他们会怎么想?他得对自己的形象负责。身为艺人,本就必须在意外形。他爱吃面包,但碳水让人浮肿,拍戏会肿成单眼皮。那就克制欲望。有一部戏,戏里要吃串,他就提前先饿一会儿。有段时间每天晚上六点过后他就不喝水了。有一阵子,他瘦到比平时的体重少了20斤。但这些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,就只是为了工作需要。
他的脸显小。很多人见到他,问他多大。他喜欢故作沧桑地说,三十多了。可人家总是觉得,这个人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。他说谢谢。但显小也不是永远都好。当要演绎一些相对需要驾驭年龄跨度的角色,看起来显小对于角色的塑造来说就是个障碍。有一次,遇到戏里几位年长的演员,他观察他们的表情,面部动作。他注意到,人的嘴角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有点往下走,他也故意学着嘴朝下去。要学的还有眼神——原来他看东西总是聚焦地去看,专注地看,那是年轻人的眼神——他再去观察那些年长的演员,发现他们看人是眯着,不聚焦,不在意,不费劲——他学起来,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好像终于有点像了。当然,他也不是只为了追求年龄感,而是因为剧情需要,他想更完整地塑造角色,不让观众跳戏。
他开始健身,有意识地练肌肉,是2020年下半年。以前他只是规律性地跑步,后来因为要在一部戏中演一个身体强壮的人,他开始健身,这个习惯保留下来,直到现在。现在,即便是在化妆间,他也会找时间做些高效的训练动作,或者跑步。但始终,总是有一些声音担心他会破坏曾经的形象。他也不想留长一点的头发,妆造时,也不想保留刘海。团队总是会和他说,你听听大家的声音,你那样更好看。有时候,他故意把自己弄得粗糙一些,的确会有人生气——而且是很多人生气——有时,还会有外界的声音对他说,你不要健身——这张脸是他的,却有无数人看着,无数人提要求——这张脸,镜子里的脸,肖战看着它,有时想,它是自己的,又好像也是其他人的。
被认为长相好看,这会不会成为他演艺道路上的绊脚石?不止一次,有人这样问他。对于好看的明星来说,这也许是个相同的困境。他也会这样想。可是他不能刻意做什么。一切都要看剧本,看剧情,看角色的需要。如果演都市剧里的一个年轻人,他想,那么故意扮丑也不对。如果剧情值得,需要他改变这张脸,那么他也有足够的热情和意愿为了角色去改变。这张脸能帮助到他,不过,他也知道,有时自己必须要付出更多。
现在,他想,也许更重要的是寻找平衡吧。喜欢他的人,一些会一直留下来,还有一些是会离开的。他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,就像小时候爬山,带着这张不断在变化的肖战的脸。

看剧本时,肖战总是会动一点小心思——如果他此刻是一名观众,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,这个故事,这个剧本能不能打动自己,自己能不能与这个角色共情——他很害怕只是成为现场的一名游魂,只是站着背台词。空洞地念台词没有意义,他知道。在一个情感充沛的古装戏里,那些天,他总是在研究该怎么说话,才能让观众为他揪心。最好的课堂,当然就是与那些更好的演员对戏。他不怕观众说他演得不如那些资深演员好。他更在意的,是在戏里是否得到进步,是否学到新的东西。
刚开始演戏时,导演怎么说,肖战就怎么做。但其实直到现在,他也还是不懂镜头里自己哪个表情或哪个动作是“好”的——他真的不清楚标准到底在哪里,也没有人与他谈论过这类问题——究竟什么样的脸才是对的?所谓的演员脸、电影脸、模特脸、偶像脸,这些神秘莫测的词语,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?他判断的标准很简单,就是只看画面本身,看画面中的那张脸能否打动自己。
现在,每到一个新的剧组,肖战都会做梦。他经常梦到导演找他,说一场戏该怎么演。“可是我连台词都记不住啊”——梦里他这样惊慌失措地想——然后突然惊醒过来。他睡不着了,下床,来到桌前,拿着笔在剧本上标记,寻找那些不合理的地方,再继续背台词。
有一个舒缓压力的方式是跑步。现在跑步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,现在总有人跟着。2016年,刚刚出道,住在月亮河,为了上镜,他总是沿着旁边的小河跑步。后来有部剧,去了浙江象山,每天晚上,只要没有夜戏,他都会去跑步。夏天很热,那时的象山空旷悠远,有一些广袤无际的农田——不像他几年后再去象山,完全变成了一副繁华的景象——农村有麦田,有稻田,特别漂亮。天黑以后,他沿着田野边缘的水泥马路跑步。马路上时常有大汽车驶来。为了安全,他会把手机闪光灯打开,让来往的车辆能看到灯,注意到人。有时他独自跑,有时和其他演员一起跑。跑一会儿,身上就会湿透,但很舒服,又热又凉快。有时跑着跑着,天上还会下起雨来——肖战此时就是肖战,他觉得——这种时候自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。
X. 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
从出道开始,从演第一部戏到现在,肖战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重复的。每一次,接到新的剧本,他也好,团队也好,总是会问,真的要接这个角色吗?的确要拍这部戏吗?他们反复筛选,反复斟酌,希望每个角色都有新的进步,每一个角色也都与肖战不同。
他自己怎么看呢。好像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。拍戏,拍广告,一些公开活动,除此以外,肖战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待着。在片场,像蝙蝠钻回洞穴,他钻进酒店房间,能不出来就不出来;平常,他待在家里,当然,除了工作时去接送他的司机,也没几个人知道他住在哪里——这像习惯,更像本能——他估计,换成别的工作,自己也不会喜欢坐在咖啡馆或者酒吧。以前他就不去人多的地方,现在的工作出奇地适配他——结束了工作就可以一个人待着——自己看剧,自己打游戏,做俯卧撑,自己想事情。

很多问题,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想明白的——当然还有那些想不明白的——肖战的办法是,那就暂时不去想。问题得自己解决,他几乎不会主动向人开口。倾诉更是个离他很遥远的词。朋友跟他说,如果有压力,就要跟别人说,去倾诉,发泄。他不赞同。能解决的问题自己就能想明白,不能解决的,说出来也是徒增烦恼。他倒宁可去做新的事情。这算是一种经验吧。人都是要不断地遇到问题,新的事情遇到新的问题,就把旧的问题忘了,这时候,答案又是显而易见的:这说明前面那个问题就没那么重要。那些重要的问题哪怕被遗忘了,也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重新浮现——像大浪打过来,孤零零一艘迷航的船,这时候,肖战觉得,依然没办法。
问题就不在于倾诉,他想。即便跟一百个人倾诉了,问题仍然在那里,没解决,它就在深夜里漂回来。
从大学时候开始他就这样,因为自己不倾诉,不愿意表达,反而成了令人有安全感的对象,他就会被朋友抓住,向他倾诉。他的角色是活人树洞。但是,一方面,为了帮助朋友,他总是听,然后听完就忘了,另一方面,他又尽量挡回去,遇到倾诉就先问:“你要说的跟我有关吗?跟我无关那就别说了,真不想听。”他觉得要帮别人保守秘密很难,所以尽量不想听别人的隐私——倾听是有风险的,秘密如果曝光,自己就是嫌疑人之一——他不想当嫌疑人,更不想到时候还要跟朋友去证明自己的诚信:“那不是我说的,我没有出卖你。”那太荒唐了,他想。
现在,他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很少。奢侈的时候,连续能有三天。这些时候,他和工作人员尽量互不联系,各忙各的,留出空间——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小宇宙里——这起初是习惯,后来成了默契,现在是事实。偶尔遇到一点工作上的小麻烦,肖战好像就能从身上随时拿出一些能量,把事情牢牢控制住。一次活动,少有的阴差阳错,已经该上台了,他们还在转场的路上,下了车,肖战往场地飞奔,主持人正在临场应变,一句一句地填补时间。走到台上,肖战记得,自己的心脏还在狂跳,他先压住它,然后把话从嘴里送出来。但是所有人都没看出什么破绽——他控制得太好、太稳了——和之前的很多次一样,工作人员确信,他真的随身带了一个小宇宙。
“我要跑了”——有时候,可能有点累了,或者突然想解解压,他开这么一句玩笑——只是玩笑,表情却认真。跑了去干什么?也许开一个花店,或者一家画廊,他说。跑到哪都行——总之一个人待着——跑到童年的厂区,大田湾的看台,或者解放碑的公交车上。也可以跑回那个推不开门的五楼,或者跑回做设计的工位上。再继续跑,就跑到童年那座山上去了。山曾经那么远,那么高,但随着时间过去,山不再远,也没有那么高了。很多人知道他叫肖战了,可那座山依然没有名字。